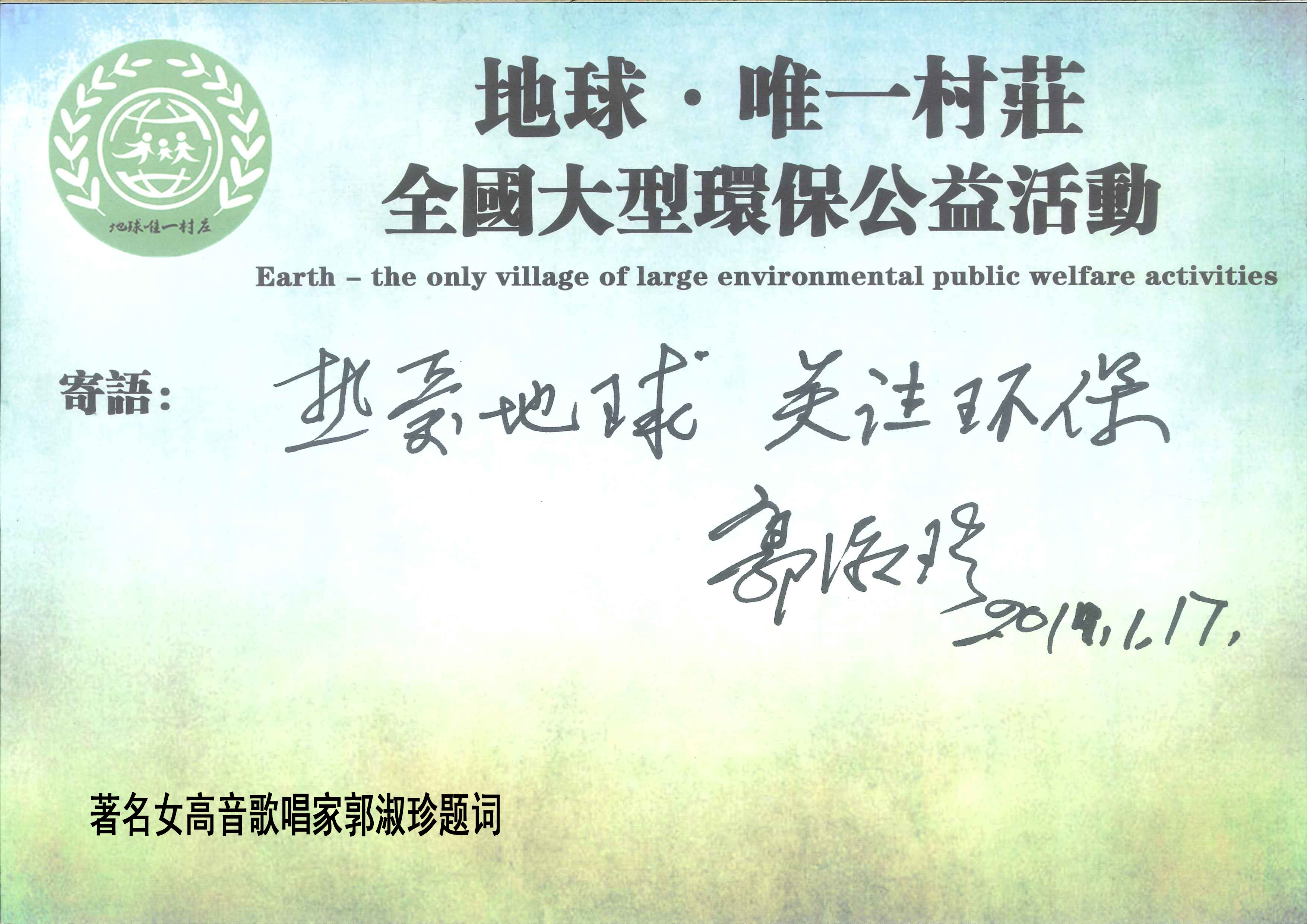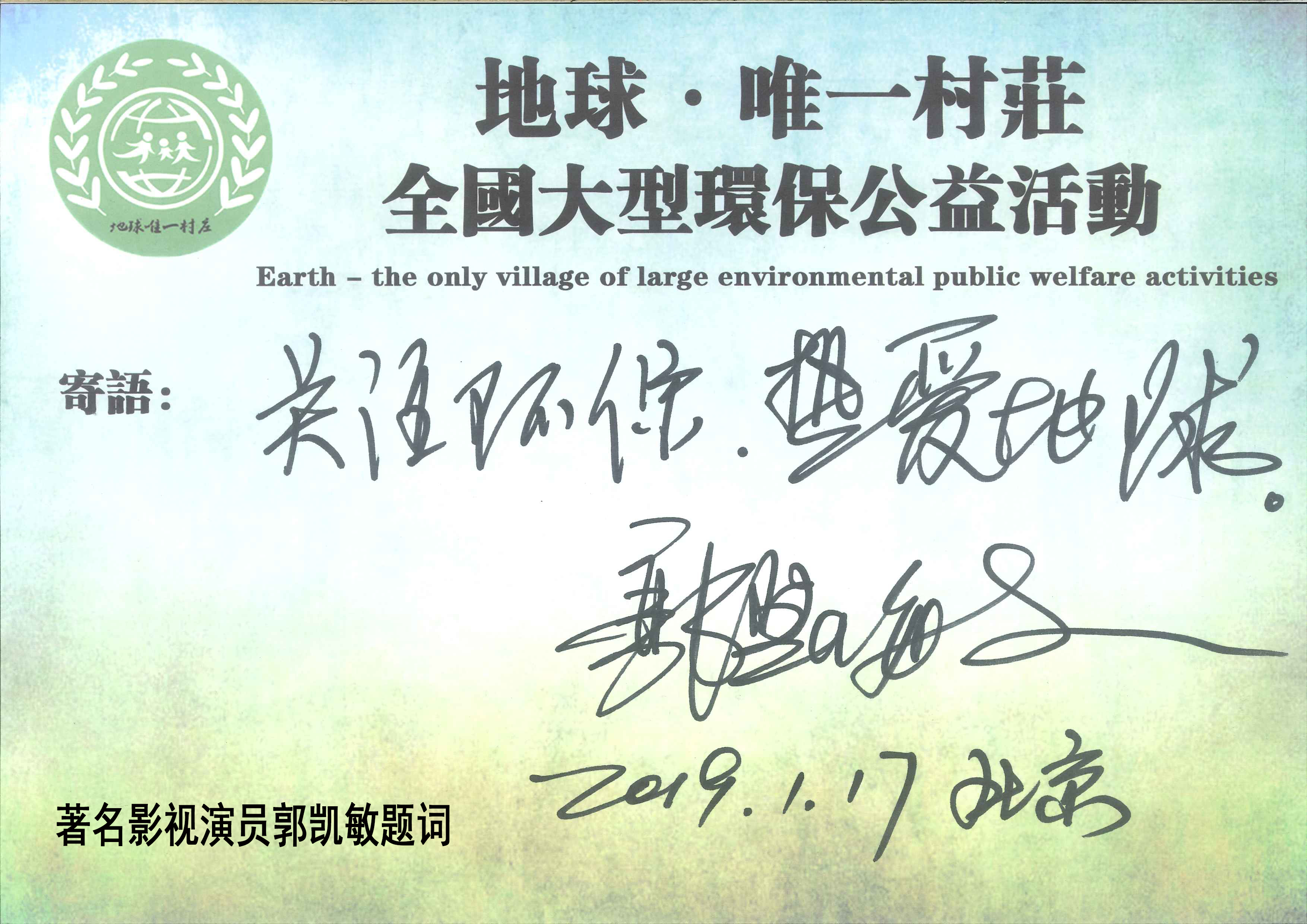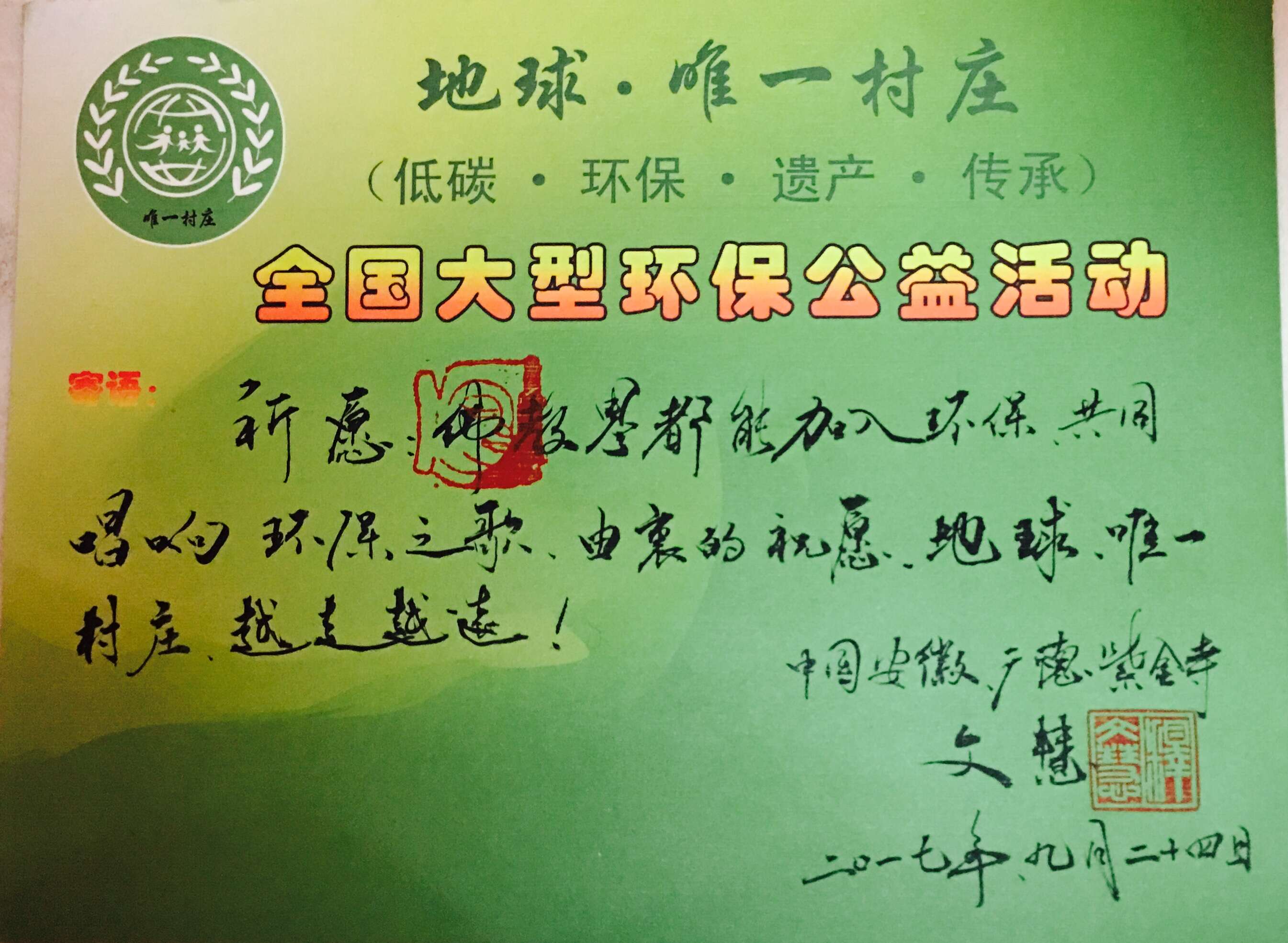河北,你被谁抛弃?
来源: 作者: 时间:2014.04.03
2月23日,河北唐山,多云间阴。市长陈学军一声令下,贝氏体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本地钢铁企业用于炼钢的转炉开始了现场拆除。
阴霾的天气和刺骨的北风像是影射着唐山钢铁工人彼时的心情,尽管这种拆除场面从去年以来早不稀罕,但每一座高炉、转炉的拆除都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不得不脱下工装另谋生路。
仅就唐山三家企业而言,3座高炉的拆除带来直接经济损失5亿6千万元和1268名职工下岗。
“这几年钢铁不景气,有点能力的早跑了,我图个稳定没走,现在马上要裁员了,你那儿有合适的工作吗?求收留!”
刘素素是涉及设备拆除的某钢厂文职人员,在和笔者qq聊天时,她发来一连串大哭的表情。
事实上,唐山钢厂设备拆除只是河北全省钢铁大手术的一隅。当天,河北省政府统一部署,在唐山、邯郸、秦皇岛、邢台、张家口5地进行第二次“周日行动”,集中拆除15家钢铁企业高炉16座、转炉3座。
这是继2013年11月24日第一次进行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周日行动”后的又一大动作。
拆掉的不是废铁,而是产值、债务和饭碗。河北辖属各城市一年以来频繁的整治清理行动在缺乏奖励和补偿机制的承诺下,这样的“壮士断腕”被染上了一抹悲壮色彩。
然而,悲壮的河北是否意识到,在缺乏配套政策供给的情况下,一轮轮产能压减风暴对这片原本增长手段单一、基础配套贫瘠的土地将带来怎样的雪上加霜?
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被炒热的今天,谁又该为这7000万人大省的损失买单?壮士断腕的河北,又该如何在压减产能、平衡就业、环境治理和转型升级的多个线头中理出一条突围之路?
产能压缩背后
3月7日下午,北京。这是全国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的第三天,也是河北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在境内外120多家媒体的包围下,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再次对河北的角色进行表态。
周称,河北不能只想从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中得到好处,而不想在生态保障、生活服务中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不能以一地小私损三地之大公。
可以说,这样的表达是对此前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京津冀三地座谈会上的积极回应,也显示了河北保障、服务北京的生态安全、生产生活的决心。
但对忧心忡忡的河北人而言,在京津尚无明确产业红利溢出和奖励补偿机制承诺的背景下,最直接的担忧是,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又要扮演牺牲者的角色么?并且,是否会让本不景气的河北更加衰败?
毕竟,红利尚在概念中,牺牲的代价却一直在付出。
虽然这个担忧往往被理解为“以一地小私损三地之大公”,但也并非没有理由。
早在去年9月,为加快大气污染治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6省市与环保部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之后,今年二月,河北发布《化解产能严重过剩实施方案》,将去年开始实施的“6643工程”进一步明确。
具体来讲包括:在未来四年内,也就是到2017年,河北将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和3000万标准重量箱玻璃。
“6643”的目标对河北意味着什么?
答案是,很难估算。因为,河北的产能统计从来都是一个迷。
以钢铁为例,《方案》中提出,利用8年左右时间,将钢铁产能控制在2亿吨左右(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前五年控制在2.2亿吨左右),2014到2015年,粗钢产能减少1500万吨。
但根据今年2月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河北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一年河北生产了1.89亿吨粗钢。
讽刺的是,如果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实施方案》提出的就不再是压减目标,而是增产目标!
事实上,河北瞒报钢铁产能数据早是行业公开的“秘密”。2012年9月,有媒体披露,河北钢铁统计数据长期造假。
某中钢协人士表示:“每年他们报上来的统计数据,经常发现粗钢产量减少、钢材产量反而增加的奇怪现象。”
究其原因,在于当压减产能的分解到地方政府,为降低减排成本、保住产量,瞒报实际产量便成为各地普遍做法。
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并对《方案》进行估算,河北钢铁的实际产能大概在2.8亿吨左右。换言之,单就钢铁一项,如果严格按照削减目标执行,未来四年就要减产超过五分之一。按目前河北粗钢平均出厂价3000元计算,直接产能经济损失已远远超过千亿。
除此之外,抛开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安置、公共服务成本大增,此中还有大量隐性成本。比如,被整顿、重组的钢铁企业和被拆除的设备往往积存大笔银行和企业债务,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执行,债务损失又是一大笔钱。
如果说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替代产业实现一定程度的弥补,在本轮河北大刀阔斧的产能削减中,社会成本的代价同样昂贵。
此前,河北人社厅厅长张义珍公开表示,2014年至2017年,全省因压减过剩产能和治理大气污染会流失约100万个岗位。
而据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段惠军透露,仅去年一年,河北因减排就已造成60万工人失业,“他们的生存是个大问题!”
巨大的就业压力不仅带来不可避免的社会风险,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需要拿出大笔财政用于就业安置和失业保险费用的支出。然而,捉襟见肘的河北又能掏出多少钱呢?
今年1月,河北省审计厅公布全省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年底,全省各级政府债务达3962.29亿元,债务率为66.94%,并称处于较低水平,总体可控。
但去年9月就有媒体报道,根据财政部驻河北专员办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中,有6个综合债务率超过100%,最高为省会石家庄,达到241%。其他5个城市债务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唐山188%、邢台153.2%、秦皇岛147%、衡水135%、张家口129%。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河北省就已将产能削减任务分解到各市,其中任务最重的七个城市依次为唐山、邯郸、秦皇岛、邢台、张家口、廊坊和石家庄。
也就是说,如果以财政部的调研报告为准,河北负债率最高的6座城市中,有5座城市在面临的沉重的债务压力下还要完成艰巨的削减产能目标。而这5座城市GDP总值超过全省GDP的50%,其中,仅唐山和石家庄两地GDP就占比38.9%。
“不光钢铁,包括水泥、搪瓷等建筑材料,还有房地产、汽车这几大板块,没有一个好消息。”唐山一位官员忧心忡忡的表示,“你要说去扶持哪个,都需要很长周期,不是没动力,而是没能力。”
不夸张地说,将“6643工程”视为河北的“壮士断腕”并不为过。然而,要思考的是,经济损失严重、失业大军激增的河北需要拿多少钱来买环境的单?这个步履维艰的工业大省是否经得起这次大手术呢?如果经不起,为何又如此匆忙的走上“手术台”?
给中央一个交代
河北的“壮士断腕”显然非出自愿。
“今天面临的压力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未来经济硬着陆、民生衰退还是能借机、借力成功转型目前还很难判断。”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牛凤瑞认为,政策出台往往受到政治和舆论裹挟,“河北的军令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给中央、社会和媒体一个交代。”
去年10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针对钢铁产能过剩,提出2017年前压缩钢铁产能8000万吨以上。具体分配到河北身上,就达到6000万吨。
诚然,作为钢铁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省际排名第一的河北,在消减产能上打头阵责无旁贷。甚至坊间戏称全球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但河北之所以捞到如此一块大“蛋糕”,原因之一被认为“沾了北京的光”。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期研究河北问题的张贵认为,环境恶化到这个程度,河北削减产能势在必行已是共识,同时“也是为北京、天津做出的牺牲,毕竟,首都是一个国家的脸面。”
但问题在于,虽然面对同样的环境污染,对于河北人而言,饭碗比蓝天更迫切一点。那么,未来还要用多少GDP和下岗工人换取北京一口新鲜的空气?
河北人的心理不平衡并非毫无来由,因为历史上,这片畿辅之地已为北京、天津做了太多的“义务劳动”。
建国以来,从行政区划上看,大规模将土地划至北京主要经历过三次。1952年,划宛平县全部和房山县部分地区。1956年,划昌平县全部和通县部分地区。
特别是1958年,为支持北京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划通县、顺义、大兴、房山密云、怀柔、延庆等10县归北京,并形成今天北京的基本区划格局。保守估计,建国后从河北划分北京辖区的土地面积约15553平方公里,约占现在北京总面积的95%。
如果说土地的划拨为北京成为国际性大城市提供了人口和产业的承载空间,那么在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突出首都门户功能的背景下,地缘的因素使得河北在自然资源、生态保护和生活服务的供给就显得“义不容辞”了。
众所周知,北京吃水靠河北。北京的两大水源地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大部分区域都在河北,且两座水库也为京冀共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河北不仅不能分走一滴水,还必须无条件地保障北京的水源供给。
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和工业用水需求量增长,北京缺水的口子也越撕越大。2008年9月,被优先安排的南水北调京石段开始向北京应急供水。然而,这样的应急很快成为常态,截至2013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从河北流入北京的淡水就达到14亿立方米,每年约占北京总供水量的8%。
更进一步的是,为了保障北京的水质,周边的河北县市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生态代价。
譬如,上世纪50年代为建官厅水库,河北怀来被迫进行了达5万人规模的移民,包括原怀来县城在内的80多个居民点和15万亩耕地被淹。后为维护水质,张家口甚至划明红线:有可能危害官厅水质的项目,不管经济效益多好,一律不批。
据悉,仅从1996年到2004年,整个张家口地区就先后投入近7亿元治理官厅水库周边的污染源。整个张家口市取缔的污染企业达486家,256家停产,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矛盾成为当地发展的主要负担。
除此以外,河北还是北京的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的704.5万常住外来人口中,河北来京人口最多,达到155.9万人。也就是说,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河北人。
京津冀往事
北京离不开河北,天津概莫能外。
事实上,天津在建国后一度曾是河北首府。然而,1967年成为中央直辖市后,先后将河北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县和遵化县部分区域割让天津,使得天津增加土地面积约7499平方公里,超过今天总辖区面积的五分之三。
与北京一样,天津也是缺水大户。尽管辖区河流并不少,但“九河下梢天津卫”因为靠海,多数河流盐分过高难以做饮用水源。并且,随着这个工业大城的不断膨胀,污染将有限的净水容量进一步压缩。
对此,从1973年河北蓟县划归天津,国家重点大型水库之一的于桥水库就自然从河北转手天津。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再次开放河北水闸,每年流入天津达10亿立方米,“天津人喝一杯水半杯来自河北”。
然而,慷慨的河北真不缺水吗?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水资源标准,如果一个地区年人均可再生水资源达不到1000立方米,就低于贫困线,而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307立方米,为全国的1/7,甚至不如干旱的中东和北非。
据统计,河北省年水资源可利用量不足170亿立方米。一般年份全省生缺水约124亿立方米,约占到实际用水量的一半。
不单如此,如同一个丫鬟,在陪侍北京、天津的岁月里,河北还充当着两地的“粮仓”和“菜篮子”,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农业大省长期被调拨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以保其需。
同时,伴随着京、冀两座城市的极化过程,越来越多的资源要素从河北流失,以至于在两地周围出现了规模达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和200余万的贫困人口的“环京津贫困带”,并且贫困至今。
“北京、天津亏欠河北太多了!”作为老河北人,提及三地历史,牛凤瑞愤愤不平,“现在都在讨论京津冀怎样协同发展,首要的问题是,京、津要不要先清还一下历史债务?”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建国后的六十多年中,当北京和天津两城激烈竞合上演当代“双城记”的时候,河北正持续大量提供着自己有限的可再生和非可再生资源,默默扮演着一个“后勤部长”的角色。当08年奥运会让北京成为世界的焦点时,当天津滨海新区在政策红利下以惊人的增长率博得眼球时,河北正在操持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打细算。
凤凰城市根据历年经济年鉴进行了数据统计,可以清楚反映三地在几十年中的经济、社会增长变化。
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河北、北京、天津的GDP比值为1:0.2:0.3;进入改革开放的1978年,三地比值为1:0.6:0.5;截至2013年,比值变为1:0.7:0.5。
直到现在,截至2013年,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方面,河北、北京、天津为1:1.8:1.4;人均占有卫生机构数1:2.5:3.7;而人均享有高效资源数竟达到1:118:236!
也就是说,占京津冀区域总面积86.9%、人口比重67.2%的河北,对于区域的经济贡献正逐渐减小,地区收入、公共服务差异却在快速拉大。
诚然,区域经济内各经济体的共生共荣需要一到两个增长极的带动。在市场经济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资源和要素必然会流向作为增长极的大城市。同时,在大城市极化初期,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往往大于辐射效应,由此带来的地区差异扩大尚属正常。
但问题在于,当地区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导致产业、社会和人才错位甚至断层时,政府本应通过资源配置缩小差异,使之逐渐形成合理、完整的区域产业链和资源布局。然而,与京、津唇齿相依的河北却在几十年中不断被行政手段剥夺掉本该属于它的资源和财富,乃至造成今天京津冀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更进一步的是,尽管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从来不缺少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但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河北是否真正存在于国家的区域战略视野中么?河北的宿命就该是“卫兵”和“后勤部长”么?
换言之,所谓京津冀,有了“京津”,有没有“冀”?
借力京津还是自主发展
河北并非没有自己的算盘,只是一直在战略摇摆中纠结。
改革开放以后,从战略定位来看,摆在河北面前的有两条路,借力京津和自主发展。但也正是因为站在岔路口的河北的犹疑不定和浅尝辄止使得自身一直在原地徘徊,错过了数次宝贵的发展机遇期。
先是借力京津,这是任何一个毗邻中心城市的区域在战略规划中往往想到的第一逻辑。
从1986年第一次提出“环京津”战略开始,河北就把希望寄于两城身上。1993年,时任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并在1994年被写入河北“九五”规划,成为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战略。所谓两环,即环渤海和环京津。事实上,在当时尚没有属于自己的海港的情况下,环京津更多地承载了河北未来发展的希望。
2001年,经建设部审定、由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对外公布。尽管此后该规划并未真正执行,但河北方面态度积极,不仅认真研究组织专家研讨,还规划了廊坊燕郊高科技经济园区和北京的大学城区作为对接北京的配套政策。
2004年2月,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召开,三地合作让人看到曙光,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也进入起草讨论阶段。此后的2006年,河北又先后与北京、天津签署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然而,在之前的近20年中,尽管围绕借力京津的战略规划不断出台,但让河北悲哀的是,大树底下并不那么好乘凉。一方面由于三地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导致具体的经济合作往往被行政高强阻隔。更重要的是,彼时京津正处在城市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的阶段,好项目不仅不会外溢,河北还往往在三地争夺中吃亏。于是,借力不成,一直充当“菜篮子”、“后花园”、“自来水管”的河北不得不寻求独立发展的路径。
曹妃甸与自主战略困境
但是,要想自主发展,哪里才是方向呢?河北的选择是,向海。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坐拥渤海湾腹地、拥有487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河北之所以没有坚定聚焦海洋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够承载海洋战略的港口。
最北面的秦皇岛港长期担负北煤南运的责任,同时由于辖属北戴河是每年暑期中央机关办公度假的圣地,无法进行大规模临港工业开发。最南边沧州黄骅港区位和地质条件不佳,难担大任。而条件最好的京唐港在与天津港的竞争中也是一败涂地。
但在2004年这一年,另一扇门被打开,一直处在“环京津”烦恼中的河北看到了自主发展向海战略的可能。
2004年12月,《渤海湾区域沿海港口建设规划》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已建设多年的曹妃甸港正式获得中央建设许可。按照规划,曹妃甸港区将是一个以大钢铁、大码头、大化工、大电力为标志的国际级港城。
此外,在北京确立“绿色奥运”的背景下,巨型央企首钢不得不搬迁。在争夺战中,唐山胜出。2005年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做出批复,同意在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作为首钢搬迁的载体,首钢落户河北曹妃甸成为定局。
同年7月,河北省正式批准成立曹妃甸工业区。3个月后,曹妃甸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并在第二年3月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至此,以项目为支点,河北在新世纪终于进入了国家战略视野。
在政策和投资鼓舞下,河北全省都在为曹妃甸的光芒悸动不已。2006年11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七大”上,决定“大力推进沿海地区开放开发,加快培养沿海隆起带”,同时高调宣布“用15年时间把河北建成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
在第二年1月的两会上,河北更是明确强调“举全省之力建设唐山曹妃甸和黄骅综合大港”。
曹妃甸成为了河北的“一号工程”。为此,专门形成曹妃甸开发议事会议制度,省委省政府唐山市官员共同参加。 可以说,曹妃甸开发让河北暂时“忘记”了京津,这片后来达到190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承载着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面向大海谋求自主的全部寄托。
然而,连决策者也未曾想到,号称投资3000亿、建设周期已达10年的曹妃甸,陨落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不仅债台高筑让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当初“大钢铁、大码头、大化工、大电力”的产业规划也相继落空。烂尾工程比比皆是,当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街景几年里变得人去楼空。
尽管此后作为回应,曹妃甸财政局局长张贺青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现金流在一些时段可能会出现紧张情况,但资金收支状况处于正常的良性循环中”,但荒凉的曹妃甸街景依旧难以打消人们疑虑。
更重要的是,曹妃甸的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标志着河北这一轮自主发展战略的破产。
产能过剩之殇
其实,无论借力京津还是自主发展,20多年辗转不定带来的最大损失不在没从京津捞到“好处”,亦非曹妃甸的投资败局。真正令人叹息的是,这个长年以来靠天、靠地吃饭的区域辗转在大战略之间,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期。
无疑,河北从来都是一个资源大省。河北平原良田沃野千里,是中国的重要粮食主产区之一。矿产资源同样丰富,主要工业原料如煤、铁、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石灰岩等构成了河北的优势矿产。
同时,河北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发展工业的省份。从1878年唐山开滦矿务局诞生第一批产业工人开始,河北慢慢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并依托其资源禀赋和区位,逐渐形成了今天以钢铁、建材、石化、医药、食品、纺织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布局。
然而,纵观世界主要资源型城市,从工业化初期到末期,都不得不面临城市定位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如果转型不顺,城市和区域的没落就在所难免。对于河北而言,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并逐渐摆脱对资源和重化工行业的依赖显得尤其迫切。
最直接的是环境承载能力,长期对煤、铁、石油、石灰岩的过度消耗使得河北环境恶化不断加速。同时,近十年来,北京、天津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上大步向前,河北已经与两地产生产业断层,即使未来北京面临功能和产业转移,河北是否有能力去承接需要打一个问号。
最重要的是,本世纪伊始,中国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加上房地产大热,强劲的需求让钢铁、水泥等基础工业迎来了“黄金年代”。市场一片大好,使得河北的这些优势行业也开始了野蛮生长。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08年,河北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最高年份高达33%。
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让长期勒紧裤腰带的河北变得“财大气粗”。从曹妃甸到“三年大变样”,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项目投资,并持续多年,这无疑给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熊熊大火再添新薪,并且,忽视了对第三产业的引导和扶持,让河北对基础工业的依存度变得越来越高。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来刺激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当投资高峰期一过, 严重的产能过剩立刻在行业显现出来。而这时,钢铁、水泥大户河北就从尴尬进入了阵痛。
“每年年底都是钢铁行的淡季,所以2011年冬天大家也没太当回事儿,想着第二年开春就好,结果,再也没等到春天。”某河北业界人士无奈地表示。
更是雪上加霜的是,环境的拐点随之到来。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大气污染愈发严峻,大面积持续性雾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其中,华北尤甚。全省主要工业城市如唐山、石家庄、邯郸长期占据全国雾霾城市榜单前列。城市环境的急速恶化以及对人身健康造成的损害使得治霾很快进入国家视野。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世界表态:中国要向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于是,还等着积压的工业品慢慢被市场消化的河北,此时不得不仓促上马。与环保部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后,河北被迫制订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削减产能计划,即“6643工程”,并直接以行政手段整治、清理相关企业和设备。
“其实本不必这样“,一位河北问题专家表示,“2008年是个非常好的契机,金融危机可以让河北工业格局按照市场规律重新洗牌,政府出台了刺激计划,就释放了错误信号,不该活下来的也活下来了”,在他看来,河北本可以避免最后以这种方式压缩产能。
其实,无论是早是晚,此时内忧外患的河北已经顾不上了:借力京津不济,自主发展受挫,产能大削减,城市债务居高不下,失业风险陡增,如果出现连锁反应后果难料......一直埋头大干的河北不得不再次抬起头,找寻救命的稻草。
产业红利迷局
让河北重燃希望来自于今年年初。
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召开京津冀三地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三地工作汇报,并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本次会议被认为是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上升到中央全面统筹的信号。信号发出,京津冀概念被空前炒热。从“曹妃甸自贸区”到“保定副中心”,围绕北京的产业承接河北的新闻铺天盖地。
在三地座谈会后的一个月,3月26日,河北迅速回应,出台《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对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以及各城市定位进行战略规划。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央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出台之前,河北各地竟已相继明确承接北京的哪些产业。
其中包括:保定将做大城市规模,承接北京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唐山上报曹妃甸自贸区,要求以曹妃甸作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廊坊重点实施央企、外企和民企总部招商;秦皇岛承接教育和医疗产业;承德打造首都经济圈高端人群疗养度假的休闲区;石家庄和沧州等也表示要以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为主要承接产业……
北京像一块待瓜分的奶油蛋糕,河北各城垂涎三尺、目光如炬。
只是,需要明确的是,北京究竟有多少产业需要转移?即使转移,在市场经济下,又有多少企业自愿选择河北?除了土地和政策,河北还能拿得出什么?
诚然,有着先天的地缘优势,看起来北京转移出的企业“顺理成章”将流入河北。但在信息化的今天,尤其对于高新产业,企业落址的逻辑更多来自于产业集聚程度和产业环境。
“市场自己会选择,高端人才也会选择,不是你想要,就能要得走,反过来对北京也一样,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规划部主任文辉接受采访时表示。
武玉是即将从北京搬离的某IT企业高管,据他表示,企业将搬往成都。为什么不是河北?“至少在成都还有那么多同行能交流交流,河北有什么?”
显然,重新回到借力京津战略的河北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城身上并不现实。何况就算能从北京的产业转移中分一杯羹,从规划、对接、落地乃至形成规模经济也需要充足的经济周期,并非一蹴而就。而在当前经济滑坡、失业率增长、民生衰退的风险愈发逼近的背景下,河北靠谁?
“远水解不了近渴,河北当前的困境可能需要中央直接的政策倾斜,包括财税、财政转移”,张贵认为,“甚至需要专项资金以补偿河北的损失。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7000万人命运的事。”
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于刃刚大胆表示,当前三地需要回归一个行政主体,可参照法国的巴黎大区的行政体制。“历史上就同属一个直隶省,经济也同属一个区域,行政也应并轨。”
但无论怎样,纠结的河北故事,还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撰文:张五明 凤凰城市编辑、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凤凰城市